情以画寄

徐悲鸿作“孙多慈”素描

少女孙多慈

徐悲鸿画作2

091330.jpg)
孙多慈自画像1
孙多慈自画像2





艺术家:孙多慈 又名韵君。
女,安徽寿县人 。
自幼即喜绘画,1931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为徐悲鸿学生 。
抗日战争期间,避地浙江南从事油画创作的同时研究国画 。
1947年后出国,后转赴台湾省,任教于师范大学 。
擅油画、素描 。
作品有《天问》、《沉思者》、《石小工》、《农作》等 。
出版有《孙多慈素描集》
(徐悲鸿he孙多慈唯一幅合作的画作)
名称:徐悲鸿 孙多慈 1946年作 喜上梅梢 立轴
材质、形制:立轴 设色纸本
尺寸:107×33cm
创作年代:1946年作
介绍:题识:1.丙戌春日写于孤山眉月楼,时方流亡归来。
孙多慈画作欣赏:




树林小屋

春城無處不飛華

091330.jpg)
孙多慈作品《姐妹》


大画家徐悲鸿的一生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女性,一个是和他私奔出国的蒋碧薇,另一个是他的学生孙多慈,第三位是陪伴他到最后的廖静文。这三位女性中有两个人都写了关于徐悲鸿的回忆录,不管是出于爱还是出于恨,他们都充分表达了他们对徐悲鸿的感情。蒋碧薇和徐悲鸿共同生活了26年,这段婚姻最后的终结是100万元现金和徐悲鸿的画作100幅,收藏古画五十幅,儿女抚养费每月各两万。这个条件不仅在当年是极其惊人的一个数字,在今天更加是不可估量,从这个条件来看,徐悲鸿对蒋碧薇是有情的,即使在他们已经水火不容的时候,似乎也没有忘却往日恩情。他在这一百幅画作之外,又送了一幅他在巴黎时为蒋碧微画的一幅画,这幅画就是大名鼎鼎的《琴课》。画面上的蒋碧薇优雅专注,色调温馨而浪漫。晚年的蒋碧薇卖了不少徐悲鸿的画以维持生活,而这幅《琴课》一直悬挂在她的卧室床头,陪伴她终了。而张道藩为她画的那幅画像被她一直悬挂在书房。蒋碧薇1966年在台北皇冠出版她的个人自传中有三分之一的篇幅留给了《我与悲鸿》,里面颇多微词,而三分之二的篇幅给了《我与道藩》,里面却不乏情深意长,而此时的徐悲鸿早已去世多年,而蒋碧薇回忆起来依然充斥了不少的爱恨情仇,并未随时间和年龄的增长而消逝多少?多少恨,昨夜梦魂中,怎么也吹不散,这是不是爱的另一种表现呢?据说蒋碧薇在知道徐悲鸿去世时还带着他们在法国时买的那一只旧怀表,泪如雨下。曾在徐悲鸿家当过保姆的刘同弟说:“徐先生走的时候,我在台湾,听蒋碧微讲的。说句良心话,虽然他们夫妻是离开了,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嘛。当然她不讲,我看她那个表情,也看得出来,她说徐先生走了,念念不忘的样子。”孙多慈这个和蒋碧薇后半生同样待在台湾的女子却一直选择了沉默。当年引起台湾岛上风波的《蒋碧薇回忆录》,相信她也一定看过,然而她并未回应,是隐忍还是无奈,抑或愧疚,后人无法窥知。那么孙多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性呢?她为什么会在徐悲鸿死后为他戴了三年的孝,她的这一举动是否表明他对徐悲鸿深切的爱和怀念呢? 孙多慈,安徽安庆人,生于1913年,出身书香门第,父亲孙传瑗曾做过孙传芳的秘书,后曾任大学教授、教务长,著有《雁后合钞》五种五卷、《中国上古时代刑罚史》《今雅》等书。母亲汤氏也任过女校校长。孙多慈姐弟三人,其排行老大。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文学绘画都有沐染。17岁毕业于安庆女中。1930年先考中央大学中文系未录取,1931年7月,以第一名的成绩正式考取了中央大学美术系,成为国画大师徐悲鸿的学生。关于她在中央大学和徐悲鸿的相知相恋,蒋碧微在回忆录中作了比较详尽的描述:“我带着孩子到家的当晚,徐先生坦白向我承认,他最近在感情上有波动,他很喜欢一位他认为是才华横溢的女学生,她的名字叫孙韵君。”徐悲鸿并非随便开个玩笑,他真的爱上了这个叫孙韵君的女学生,并且在当时不仅仅是家庭甚至是社会上都闹得风风雨雨。好事者添油加醋,捕风捉影,一时满城皆知。当时的不少小报都对这段恋情进行了跟踪报道,更有好事者将此事传播到安庆,在孙家也引起了轩然大波。孙父更亲自赴南京会见徐悲鸿夫妇。事情并未往好的方向发展,他们的这段三角恋情,最终以三败俱伤收场。徐孙二人曾经合作过一幅非常有名的画作《台城望月》,画的是玄武湖畔的台城上,徐悲鸿席地而坐,孙多慈则侍立一旁,颈间一条丝巾随风飘扬,天边一轮明月朗照,极具意境美感。坊间流言此画被蒋碧微藏起,后毁于战火。但是蒋在回忆录中写道:“至于那幅《台城望月》,是画在一块三夹板上的,徐先生既不能将它藏起,整天搁在那里,自己看看也觉得有点刺眼。一天,徐先生要为刘大悲先生的老太爷画像,他自动地将那画刮去,画上了刘老太爷。这幅画,我曾亲自带到重庆……妥善地交给了刘先生。”具体真相如何,只有当事人清楚,但是此画失传,的确是一个遗憾。徐悲鸿的南京公馆落成时,孙多慈送来枫苗百棵。但蒋碧微得知此事后非常气愤,让佣人把枫苗全部折断烧毁。徐悲鸿面对此事,痛心无奈之余,遂将公馆改为“无枫堂”,称画室为“无枫堂画室”,并刻下“无枫堂”印章一枚作为纪念,钤盖于那一时期的画作上。1934年徐悲鸿与孙多慈等去天目山写生,孙多慈曾赠红豆一枚给徐悲鸿,徐悲鸿用金子镶刻成戒指,内刻“慈悲”二字,这个戒指他一直戴在手上,直到和廖静文结婚才摘下。1935年,孙多慈毕业于中大。在徐悲鸿的帮助下,她于毕业之初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个人画集《孙多慈素描集》,宗白华先生作序写道:“落笔有韵,取象不惑,好像生前与造化有约,一经晤面,即能会心于体态意趣之间,不惟观察精确,更能表现有味,是真能以艺术为生命为灵魂者。”徐悲鸿更为她多方奔走,争取公费出国名额,后未成行。
1938年7月31日,徐悲鸿在广西登报和蒋碧微脱离关系,随后托友人沈宜甲到孙家提亲,却遭到了孙传瑗的坚决反对,从此徐悲鸿与孙多慈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38年元旦,王映霞与浙江省政府秘书李立民的女儿李家应相遇。李家应便托王映霞为孙多慈找个对象。王映霞遂不顾郁达夫的反对,将孙多慈介绍给了许绍棣,许绍棣是浙江临海人,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妻子因病去世,留下三个女儿。据说他貌不惊人,个头还没有孙多慈高,而孙肯嫁给他,多少带点寻找依靠的成分在。当时正值乱世,许绍棣也是孙传瑗的顶头上司,因着孙多慈的关系,对孙传瑗非常照顾,每当日机空袭丽水城,许绍棣总是安排孙传瑗夫妇住到建有防空洞的丽水中学宿舍。当孙传瑗提出辞呈,要到长沙去,许绍棣立即批准,除命令财政处支付3个月薪水外,又特批大洋80元,作为补助金。这一切都令孙多慈深为感动。也因为许的关照,让孙多慈在乱世能得一清净,潜心作画,暂时忘却身世漂泊之苦。孙多慈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写道:“急雨狂风避不禁,孤舟一叶独沉沉。”由此看出,当时的她多么彷徨和无助。而此时的徐悲鸿正在印度讲学,后去新加坡,一去四五年未归。许绍棣的出现恰恰使她得到一块浮木,可以依托着前行,寻找上岸的方向。作家琦君在孙多慈去世后曾写过一篇悼念文章叫《日边清梦断》,其中这样写道:“回想三十年来的情景,就有如三十天,甚至三天内的事,能说人生非短梦一场吗?记得初识您时,是在杭州春日的西子湖头。那天你穿一身浅绿旗袍,披一件白色哔叽短外套,在湖堤边桃花柳絮中间,冉冉地向我走来,由许先生介绍我们见面。我呆呆傻傻地望着您,您那出尘绝俗的高雅风度,和我由久已闻名对您所塑造的印象,恰相符合……”从这段描述可以看出,孙多慈在杭州的生活是稳定而安逸的。当徐悲鸿回国的时候,孙多慈已经结婚生子。1938年徐悲鸿在香港写下一首《怀孙多慈》:“夜来芳讯与愁残,直守黄昏到夜阑;绝色俄疑成一梦,应当海市蜃楼看。”可算是对这段爱情的最后诠释。1947年春,孙多慈旧地重游,回到南京,独自来到位于鼓楼傅厚岗的坡路上和四牌楼中大校园内外时,心情惆怅而复杂。此时徐悲鸿已与廖静文结婚。孙多慈的表妹陆汉民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我至今记得1947年春,表姐孙多慈带着大儿子许尔羊(次子许珏方尚小)从杭州来南京小住了几天。这是充满悲情的寻梦之旅,是为了寻觅昔日的爱情之梦。她和儿子在我家吃了顿饭,叙了别后之情。那天下着淅沥春雨,远近弥漫着迷蒙的雨雾,路边法国梧桐树透着新绿,行人都撑着雨伞或披着雨衣。我表姐哄睡了儿子,撑着伞,独自来到徐悲鸿家院墙外,久久地徘徊,雨雾中的洋楼门窗关着,冷寂无声。主人已去了北平筹划北平艺专复办事宜。他忙着事业。而孙多慈旧情难忘,心境凄凉。她背着丈夫许绍棣前来傅厚岗为的哪怕再看旧日恋人一眼啊!可是生活的潮水已淹没了前尘往事,我表姐是含着眼泪离开那洋楼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她一步一回头,步履沉重……”徐悲鸿与廖静文结合后,孙多慈曾在一幅红梅图轴中题写“倚翠竹,总是无言;傲流水,空山自甘寂寞”的词句,表露寂寥伤怀之情。据孙多慈遗留下的日记披露,她内心最爱的人还是徐悲鸿。在她弥留之际,她在挚友吴健雄的手上比划了两个字,这两个字就是“慈悲”二字。这真是一段让人唏嘘不止的悲剧爱情。 1949年之后孙多慈随许绍棣迁居台湾,多次在台北、香港举办个展。苏雪林在文章中写道:“民国三十八年,我自大陆来港,供职香港真理学会,隔壁有个思豪饭店,隔不上三天便有一个书画展览,我常溜出参观。虽然也有几个画展不大像样,但大多数很好。这是我在大陆时所难餍足的眼福,也是流亡生活中意外的奇趣。1950年春间,多慈自台湾来香港,举行画展,也以思豪饭店为会场。这一次她展出国画五十余幅,油画水彩二三十幅,素描十余幅,还有若干幅的书法。我可说这是思豪饭店自有画展以来,最为热闹的一个,整个港九都轰动了,每日来参观者络绎不绝,几乎踏破了饭店的大门;也是最为成功的一个,展出的百余幅作品,除了非卖品以外,都被订购一空。”那时的许绍棣如日中天,成为台湾政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在他的荫庇下,孙多慈又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当研究生,后去法国国立美术学院从事研究。回台湾后在台湾师范大学任教授,并于1957年获台湾教育部美术类金像奖。她为人友善真诚,朋友很多,苏雪林赞她“与之相对,如沐春阳,如饮醇醪,无人不觉她可爱”。琦君夸她:“与她将近三十年的交往中,我们很少正面讨论人生问题、感情问题,我却感觉得出来,她内心有一份炽热的感情在燃烧。这从她的乐于助人,对青年学生的爱护协助,以及对人世善恶之分明看得出来。”孙多慈在台湾交游广泛,苏雪林、琦君、林海音、陈香梅等都和她是好朋友,从中不难看出她为人的宽厚及友善。在台期间,她不仅教书育人,也在世界各地游历与讲学。1963年7月,孙多慈应聘为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美术系主任,罗家伦请孙多慈为“台湾国史馆”绘制大型历史油画,有《黄兴马上英姿》《黄兴与夫人徐宗汉》《秋瑾》《陈英士》《卢构桥抗战》等。苏雪林在《孙多慈女士的史迹画及历史人物画》中对她评价极高:“多慈是学西洋画出身的人,对于造型之学,筑有坚实的基础,她每画一名贤之像,必先求前人所作,参伍折衷,求得一个比较近似的标准。这比较近似本来是难说的,我们既未及身从古人游,前代画家所作,又大多出于想象,有什么标准可以依据?所以她想出一个不画形貌而画灵魂之法。古人的灵魂寄寓于他们自己的作品,熟读他们的作品,则可以想象出他们音容笑貌,最后神光离合之间,整个法身,倏然涌现,摄之毫端,也许比当时对面真,更能肖似,所谓‘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所谓‘求之于牝牡骊黄之外’者是也。”苏雪林与孙多慈是安徽老乡,又都是学画出身,只是苏雪林后又转攻文学。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期间更是同事,画室和书房一北一南,又是邻居,缘分和交情都可谓深矣。她的评价从侧面反映了孙多慈在台湾画坛的地位和作用。
孙多慈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女画家,与潘玉良齐名。但潘玉良专攻西画,孙多慈则和他的老师徐悲鸿一样中西兼修,在两种绘画领域纵横游走,挥洒自如,都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作为徐悲鸿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女人之一,孙多慈虽然没有写出长篇的回忆文章,但是她在画艺上的刻苦钻研,永不放弃,我觉得她是在以另一种方式向她的老师致敬。台湾的徐派弟子很多,他们都在努力地传播着徐悲鸿的艺术主张和教育理念。其中以孙多慈最为明显。正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艺术之广博浩瀚诚无涯际,苟吾心神向往,意志坚定,纵有惊涛骇浪、桅折舟覆之危,亦有和风荡漾、鱼跃鸢飞之乐,果欲决心登彼岸者,终不当视为畏途而自辍其志也。”1953年徐悲鸿去世,孙多慈悲伤之余,绘制了画作《春去》。画面是:春寒陡起,山雾萦绕,一个纤细柔弱的女子孤身独坐溪边,看着溪水潺潺流过,落红漂转,一片凄凉之感。很多年前还在南京中央大学时期,徐悲鸿曾写下一首诗送给孙多慈:“燕子矶头叹水逝,秦淮艳迹已消沉。荒寒剩有台城路,水月双清万古情。”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流水落花春去也,为这段爱情画上了一个凄凉的句号。在徐孙相识之初,徐悲鸿曾刻一枚“大慈大悲”的图章,似乎从开始就预示着这段爱情带有一份淡淡的哀愁。
1970年,将近60岁的孙多慈被查出得了癌症,经过几年的治疗调养,还是没有敌过病魔,3次赴美开刀治疗,也未痊愈。最后于1975年2月13日病逝于美国洛杉矶其生平好友物理女王吴健雄家中。时年63岁。台湾作家琦君评价她:“如此孤高标格,归魂只合傍梅花。”从孙多慈留下的几首赠给徐悲鸿的诗中也可看出她一生的无奈和辛酸。“极目孤帆远,无言上小楼。寒江沉落日,黄叶下深秋。风厉防侵体,云行乱入眸。不知天地外,更有几人愁。”“一片残阳柳万丝,秋风江上挂帆树。伤心家园无穷恨,红树青山总不知。”这些诗道出了她爱不得、恨不能的人生悲歌。孙多慈去世后,许绍棣默默地守着挂满四壁的孙多慈画作,孑然一身地生活在台湾,常怀“望故乡之渺渺”的伤感,更集唐人句写成《乡情》多首,其中有云:“几多人物在他乡,枕绕泉声客梦凉。白首思归归不得,海天东望夕茫茫。”在《八十感怀》诗句中写道:“览镜白头嗟耄及,可怜归计日迟迟。”表达了孤身一人的悲怀。去世的前几天,病榻上的许绍棣还写了一首《踏莎行》(寄诸好友):“一室羁栖,孤零滋味,伤心触景情先醉,人生安乐总无方,凭栏不觉洒清泪。”这首词还没有写完,他就撒手人寰。1980年,许绍棣病死台湾,子女将他与孙多慈的骨灰合葬在阳明山。而1978年去世的蒋碧微也葬于阳明山,她去世的时候,墓碑上并无儿、女、孙儿、孙女的名字,说明她去世的时候,身边并无直系亲属,多么孤单的离去。如今看来,这两位和徐悲鸿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奇女子的身世真是让人不胜唏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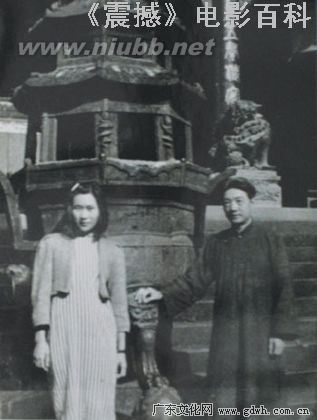 1946年,听说徐悲鸿娶了湘妹子廖静文,孙多慈画了一幅红梅图轴,在画上题词:“倚翠竹,总是无言;傲流水,空山自甘寂寞”,这就是她心情和人生的写照。后来,徐悲鸿在梅枝上补了一只没有开口的喜鹊——欲说还休……
1946年,听说徐悲鸿娶了湘妹子廖静文,孙多慈画了一幅红梅图轴,在画上题词:“倚翠竹,总是无言;傲流水,空山自甘寂寞”,这就是她心情和人生的写照。后来,徐悲鸿在梅枝上补了一只没有开口的喜鹊——欲说还休……【壹】慈悲之恋
在徐悲鸿与孙多慈之间,我感觉,最初她对他,应该是对大师、名人的崇拜之情。
在逐渐的交往中,那个本来有些被神化的男子,表现出怜惜和关爱,敏感的女孩子不会察觉不到,一来二去之间,她就把自己交出去了。
首先交出去的当然是信任,她相信他的见识,他的判断,他的境界。她像海绵,吸收着他,像向日葵,追逐着他。
徐悲鸿不知不觉间也把她当做自己的作品了吧?大大小小的事情,几乎都由他代为做主。小到孙多慈求学期间的课程,由他酌情选定;工作之后孙多慈办画展,徐悲鸿前后张罗,拿主导意见。筹备期间孙多慈本来想把中国画也放进来,大师坚持只要西洋画,既然叫西洋画展就名副其实,而且女画家的西洋画展在那时候也更有特点,孙多慈依计办理,画展果然成功。更不用说出书、出国这样事关前途的大事,徐悲鸿更是一一规划。
他们之间的感情产生于蒋碧薇及众人发现和议论之前、之后或者同时,恐怕连他们自己都界定不清。但我始终相信,有那颗种子才会发芽,不会像孙多慈辩解的那样,我们本来没有什么,大家都这么说,师母也来兴师问罪,索性就成全大家吧。这实在是找个理由,来解脱自己的内疚和不安。
慈、悲之恋,越来越不可遏制。1934年10月,金秋时节,徐悲鸿带学生去天目山写生。因为出国办展览,跟学生分别将近二十个月。尤其是慈、悲,颇有点“小别胜新婚了”吧。于是在一些僻静处,两人情到浓时,不由得深情拥抱相吻,这样的一幕还被一个带相机的同学收入进了镜头。
就在天目山上,层林尽染,暮霭深处,孙多慈在山间的小路旁,发现了一树红豆。她伸出纤纤玉手,满怀愁思和柔情,郑重摘下相思豆,娇羞地捧给老师,那就是少女的心思——爱的箴言。
徐悲鸿的反应很配合,非常少年。一回到南京,就到银楼打了一对戒指,把红豆镶入其中,一个刻着慈字,一个刻着悲字。一个中年男子,还能生出这样的情愫,做出这样浪漫的举动,是幸,还是不幸?
徐悲鸿观音像背后的故事


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mw748219